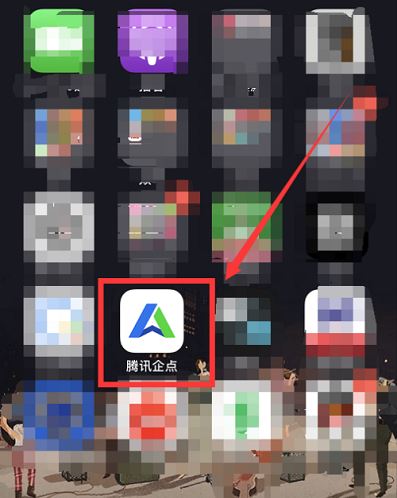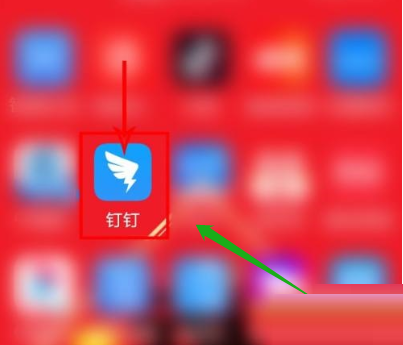文:言郁华
零落 第二部分
 【资料图】
【资料图】
太阳远下,半悬于西边的大海上,绛色的天中,道道光束击打着被海风刮碎的云脊。早晨飞出的远洋鸟乘着最后的陆风滑翔归来,时上时下,划出了一布疏散的线网。归鸟的叫声在天地间此起彼伏,宣告着白日的结束。
广南的六月,正是太阳最烈的时候,也只有在傍晚,日头才会隐去炎曙,显现出它滋养生命的温情。博安将头上沾满汗水的麻巾解下,拄着铁铲,望向西方的洋面。
“碎月州等,座乎西极,梵梨呼诸其曰〈日没处岛土〉……”博安瞭望着闪着紫色光芒的汶东海,忽地想起了出击前,船上的文化指导员在战斗预备会上讲的内容。博安尚记得那个出身云杭地区的小个子指导员在摇晃的船上,一边在黑板上歪歪扭扭的板书,一边唾沫横飞的用他那西土口音浓重的诸涯官话和水手们讲课的样子,“恁等看看这个地方,就是碎月龟儿子老家咯!娘牝(pǐ)戏的碎月岛里头,有个喊做晴岚地方,建个公司买了好多人抓去广云当奴婢……”这位指导员小品似的授课,很受粗豪惯了的水手们欢迎。尤其他那不时冒出的几句方言脏话,更不时让聚在前甲板听课的官兵们爆发出阵阵大笑,甚至连舰司、大副、炮术长等“大军官”也时不时钻入水手群中,来听这位指导员的课会。
想到这里博安长叹了一口气,在昨日晚间的暴风中,那位指导员在甲板上向落水士兵丢着木板和物资的时候,一个浪头打来,将他带入了轰鸣的暗洋。最终,他还是未能踏上广南的土地。
望着大海磨了一会儿,博安将解下的头巾在脖子上松松的绑了,继续挥动铁铲,为已近完备的炮兵阵地防垒垫上最后的几扇土。在他的身后,就是从坐滩的巡洋舰“松羯号”上卸下来的一门24磅海军炮。眼下这门1.5吨(注:此计量单位与本位面相同)的铸铁大家伙,正坐在小丘上,炮口冷冷的戒备着洋面。附近的几座土丘上,也错落着从战舰上卸下的重炮。这些不便在陆上机动的海军重炮没有放到营地内,而是安置在营地西南,警戒着碎月水师可能的突袭。
至今为止,海面上还没有出现那令人恐惧的蓝色新月旗。
博安将最后的几铲土按在防垒上,再重重的拍了几下,让土夯的更紧密些。远走几步,望见炮口略高于垒墙的顶端,寻思着应当差不多了,便越过垒前的防弹壕,三步作两步跨上了土垒,走过炮位,落入交通壕内。
一进交通壕,倒是带下了一堆尘土,落到了一群正围坐着玩牌的士兵身上。这六七个兵卒混杂穿着水兵和陆战队的制服,有的还光着膀子,打牌打的正起兴。忽的被一堆尘土弄的灰头土脸,几个打的急的便喊将起来:“直娘贼,怎个这么不长眼!”“扑你母个臭膣(gī)……”“我测你的马……”一时间响起了几声极富地方特色的粗口。但在看到博安的眼神后,兵士们个个便住了嘴。
一个光着膀子的士兵,头上带着一顶陆战队的遮阳盔,正在专心致志的看着手上的牌,丝毫没有注意到博安正站在他身后。
“两对骑兵,一个步兵,一个炮,牌不错啊。”博安笑道。
“是啊,就是补给消耗大了些,如果打得好把补给点拿过来倒是稳赢。”这士兵边看牌便说着,“下盘老哥要不也来一把,一盘就赌根嚼烟或两根卷烟,不算太坑……”说了正要出牌。
博安突然大吼一声“暂四营猎兵连,二排二等卒钟提武,立正!”
这士兵霎时从地上站了起来,手里却还紧握着牌。
“其他人也起立!”围坐着的一帮人也赶忙站起来。“你们几个差不多得了啊,炮垒也不搭好,整个骨架就跑来里头打牌,到时候碎月佬的水师打过来了,陆军登陆了,你们用脸接枪子,嗯?”“博副排,咱们弄下来这几门重炮,放在碎月陆军那边都够搞个小要塞了,他们要是上来就用葡萄弹轰呗……”一个穿着炮兵制服的小辅兵细声说道,“你看,玩军牌玩的。要是对面一发舰炮把你炮垒打垮,炮子突你脸上,你被炮子打碎了,是不是能自个把自己拼起来?”博安大声斥道,那小辅兵便唯唯诺诺的不敢出声了。
随即博安喊了声:“全体都有,《阵兵要指》唱!”顿时,一片尚称得上整齐的然绝不动听的豪放歌声响起“伟哉万胜我天军,顺天救民除水火。阵战行往几须知,一者不可扰百姓……”唱完了一曲,博安又问:“第五条为何?”“五者任职要尊令,事必躬力十分行……”众人回答的声音明显较唱歌时要小的多。
“行了,这次我也不和连部那边讲,不然你们这两星期的烟草补给又得泡汤,好自为之。去把土给我夯好点,快快快!”博安催促着,将士兵们赶出交通壕。“对了,记得挖土从防壕里挖,你们这帮懒狗别把前边的伪装植物给挖开了!”博安大声的补了一句。喊完,便顺手从组员们放在壕沟内的补给里随机抽取了一条嚼烟,掰一段嚼了起来。烟草的涩味和果干、香料的甜熏气顿时在口腔中弥散,博安哼着小曲,爬出交通壕,向着另外一处炮阵地走去。
太阳没下,博安领着筑垒的士卒们回到了营地。在一通总结后,士卒们便一哄而散了,博安也带着二排的人向着本排的营地走去。
一到营中,却是看见留守的一等兵车守仁和一个穿着短衣的汉子用毛巾包着锅柄,用力的抬着铁锅,将锅中的奶茶倒进一个大木桶里。远旁一个黑黑的瘦高少年正坐在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上,用铡刀切着一大堆苜蓿。
车守仁和汉子将锅中的奶茶倒完,望见博安等人,便将铁锅放下。车守仁敬了个军礼,向博安介绍到:“博副排,晚上好。这位是吴林,温台人,明天给咱们排当向导的。”吴林听罢,赶忙和博安鞠躬:“博军爷好,小的在这广南混了几年,附近的水土却是熟悉,梵梨话也晓得几句。”博安见吴林鞠躬,赶忙上前扶着,用白明话说到:“阿欸,吾等皆是老乡,莫地恁客气!老哥哥,年齿几多哉?”“噢哟,靡(不)敢当,靡敢当,哪里敢在大军前称哥哥,小的不过三十有二而已。”“讲么子客气不客气,小军我二十,彼帮管带(我手下)的军士没个大多哥哥尔(你)的,细(年纪小)的很。又远来地方不熟,这日子还待哥哥照拂几个。”“喔哟,如何细得(年纪都这么小)?真是英雄出少年哟.....”一番马屁下来,两人的关系迅速拉近了。
博安和吴林聊着的这阵子,随博安归来的士兵们皮袋里的水已喝完,早就耐不住渴。看着支援连尚未抬饭菜过来,便拿着随身带着的椰壳碗在木桶里舀起奶茶来喝。博安将自携的椰壳递给吴林,自己拿了把大马勺,蹲坐在一旁慢慢啜着。这时博安瞥见那少年仍在铡着苜蓿。博安吹了吹勺中的茶,一气饮尽,起身向他走去。
接近了少年,见他仍在铡草。“小鬼,叫什么名字?”博安问道。“博军爷好,我叫也奢,军爷喊我阿也就好,吴叔他们平时都这么喊我。”少年说着,手中的动作没停。“好,阿也你不去喝点茶吗?”“桐涯的茶我喝不大习惯,里面太多香料和醍醐(奶制品)了。”“哈哈,你是梵梨人?”“我妈妈是,我家就在东南边七八里的地方,我还能说碎月话。”“可以,多大了?”“十六。”“十六.......当年我投军也是这个年纪。”
说着说着,也奢已经将一大堆苜蓿都切成了小段。随即站起身来,将切成细条的苜蓿用草叉扠成一个高堆,再轻轻用叉齿拍打草堆,将其压实。
博安奇道:“这草怎么这么多?少说有六十斤,用来喂豫象的吗?”(注:豫象既本位面的蒂洛斯侏儒菱齿象,拉丁文学名:Palaeoloxodon tiliensis,在云澜位面是特产于桐涯的役畜)“不......豫象可没吃的这么多。”也奢说到,又吃力地扶起了本来当做坐垫的一大袋碎玉米,哗啦一下倒进了一个巨大的木盆里。倒完一袋,木盆仅装了三分之一不到。也奢复走去物资棚下,准备再拖一袋谷物出来。
博安见状,走上前去,三下五除二便将也奢准备拖出来的谷物抗在了肩上,倒到木盆里。也奢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谢谢博军爷。”“接下来还要拌些苜蓿是吧,像喂马一样?”“是,兕(sì)对饲料要求很高,不像牛那么好养,但是比马好喂一点,不用天天给它洗擦。”
博安疑惑的问:“兕?那是什么牲畜。”也奢笑到:“长的和犀牛一般,就是角和体型要大上许多,性子也比犀牛要温顺。”(注:此处指的兕乃本位面的王雷兽,学名Brontotheriidae,和本位面“兕”一词所指的圣水牛不同。)博安想了想,还是没想象出兕的样子。
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望舒(注:云澜的卫星,比月球稍大)也随着天色的昏暗显出清辉,一个晴朗的夜。外出汲水打樵的军卒陆陆续续的都回到了营中,支援连也终于炊毕饭菜,分发到各连的营中。
之前被抓去支援连帮厨的夷则也和人抬着饭菜回到了二排,还随着十来个恢复的差不多的兵士补充进了二排。博安将这新来的十来个人分别安排了夜宿的帐篷,安插到人力不足的班里。熟练安排完这一切,便宣布开饭。
饭菜十分简单,糙米饭、由从周边梵梨村子购买的鲜菜加上船带的干肉乱炖的咖喱、咸粟汤。由于陆军的炊事用具和火兵(炊事员)在兰石号的倾覆中损失了许多,营部只好将松羯号的锅具无论大小都收集起来,再加上抓来的不少小辅兵帮忙备料烧火,终于完成了这一顿饭。对于吃惯了冷饼干和干肉的海军官兵来说,能吃上热食已经是十分优良的待遇了(海上经常因为大风、防火等原因,不许在船上做饭)。但是对于大多数时候都能吃上热饭的陆军而言,却是颇有微词,许多安插进二排的陆军猎兵对于饭菜(尤其是乱炖的咖喱)显露出了难以形容的脸色。
二排的众人正围着饭桶吃饭,博安趁机仔细观察了下新补充进来排里的士兵们,有几个他熟悉的面孔,是原来松羯号上的桅杆射手。还有一个方攻部队的女兵,也和众人蹲着默默吃饭,偶尔同旁边陆军出身的士兵说两句话。
博安收到的补充人员名单写了,她原本是兰石号上方攻部队(注:魔法支援部队)的少尉(注:少尉是桐涯方攻部队的基础官职),名叫珊粲婕。兰石号上面带着的方攻部队共一个小队14人,活下来了9个,相较于陆军近乎三分之二的损失率,方攻部队的损失不可谓不小。但是方攻部队作业所用的各类大魔力器械则全没剩下来,幸存下来的方攻士们只得负责医护方面的事务。
夷则在回来时和博安说了,明天将有大行动,猎兵连应当还是惯例,负责侦查和火力准备职务。但二排的具体作战任务,则要等从连部开会回来的奈师德传达了。
而更为令人注目的,则是正在大吃糙米饭的也奢。也奢抱着大木碗,已经连吃了五碗拌着咖喱的米饭了。坐在一旁的吴林见此,忍不住斥责起来:“你少吃点,别人明天还要打仗,你又只带路不拿枪,哪里吃得这么多?”随即便在也奢的头上重重拍了两下。
拍完后,吴林对兵卒们抱了抱拳,道歉道:“还望各位军爷海涵,这庄头隼利家剥削特厉,平常我们穷人和他干活收作料便算了,但却连稻谷、粟米都不给种,说是劳什子浪费人力、影响收获产出,只准我们种些甜薯、芋头、玉米过活。但凡发现种米的,已有的米谷全没收了不论,还要你上贡一大笔罚金。一旦交不起,便喊人先抽你三五十鞭,再发到甘蔗田里干活,三五十鞭!好多人就这样被抽的发疽死了。”说至此,吴林低头落下泪来。
也奢听了,也放下勺子,说到:“那正是,听我祖母讲,晴岚人来前,好歹不时吃得糙米。这晴岚人来了,八角、胡椒是越来越多,反而大米吃不上了。天天啃芋头啃的嘴里发涩。真不知道以前的那么多大米都跑哪去了。”听了这一番话,兵士们都沉默了,不知当怎么接话。许多人想起了自己的过去和加入革命军的原因。未加入军队之前,自己何尝也不是在地主和苛捐杂税中苦苦求活。
正在沉默中,忽然不远处传来了传令的小锣敲击的声音:“猎兵一连二排副排长博安、向导也奢,出来接令!”博安听到锣声,将饭碗放在地下,便走去接令。也奢也放下饭碗,摇晃着起身,跟着博安。
出了二排营地,从其它排的几座帐篷间穿过,两人到达了连营地的空地集合点。看见奈师德正和两个营部的宪兵站着,两个宪兵手里都拿着枪,却是押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在三人的身后,还有跟着四个穿着炮兵制服的人,其中一人牵着一头长着巨大角的动物,动物的背上还杂七杂八的背着东西,看形状貌似其间还有一门小炮。
博安心中暗叫不好,第一反应却是奈师德整了什么大动静,居然将宪兵给引来了。但仔细一看,却又发现宪兵和奈师德的脸色并非十分严肃,心下却稍稍放松了点。
而也奢的脸色却在见到小女孩身影之时便咬牙切齿,嘴里大吸一气,恨不得冲上前去,但又看到宪兵手上步枪刺刀在火前的闪光,却又忍着同博安向前走去。
到了三人跟前,一个宪兵先发问道:“你们就是博安和也奢是吧?”两人回答是。宪兵再复问道:“也奢,你看看这女孩是否你的妹妹?”也奢几乎在宪兵问完的一瞬间便肯定的半喊出声:“是的是的,两位军爷,这个就是我的妹妹椰雫溪。”也奢又想续问为何将她押着,奈师德开口了:“今天战列连那边派人去打柴的时候,有个向导是卧底,想偷偷逃跑去菩拂云庄报信,被他们发现抓回来毙了。营部知道了这件嘱咐我们加强警戒,在附近巡逻。这孩子就是给附近巡逻的捡到的,当时她就往咱们营地的方向走,一问说是从东北边五六里(注:桐涯一里约比本位面的一公里略长)一个叫散勒的村子跑过来的。巡逻的不敢怠慢,怕是探子就拿回营地里查明身份。”
也奢一听,几乎是当下便用梵梨话向椰雫溪大骂起来,椰雫溪也不出声,低着头在那一言不发。奈师德苦笑着看着这一切,转头和宪兵说到:“应该是了,把这姑娘的绑绳解开吧。今晚让这两孩子在我们排里睡着,二三十个人看着,想报信也跑不了路。”
宪兵将椰雫溪绑在手上的麻绳解了,也奢估计是骂的气急,又吃的太饱,一时吐了出来,跑出二十来尺远大吐了一番。呕毕起身看着地上从自己胃里跑出来的糙米、咖喱混合物,显露出懊恼又夹杂着苦闷的表情,转过头来,用桐涯话说道:“天杀的,却可惜了好米!”
在场几人却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奈师德喊到:“你拿个勺刮点上面没沾到土的却还是能吃一顿!”见也奢却真的想用手去捞那呕吐物上的大米,德安忙走去阻止道:“行了行了,回去还有饭来着,我喊他们预留了些的。”
德安劝住了也奢,转过头来,奈师德和两个宪兵说了几句,一个宪兵拿出一张纸让奈师德签了字,两人便走回营部了。德安走向奈师德,说道:“你差不多得了,你没当兵前还不是几个月吃一次大米,要是你当时吐了别人喊你捞你不也屁颠颠的去整。”奈师德却是故意板着脸说到:“忘记和你说了,我家以前是米商。”
德安顿时不知道说什么了,只得招呼随行的几人牵着牲畜回营。
回营路程很短,德安简短的问了问奈师德拿到的确切作战方案,得知二排要在明日的作战中和三排共同作为猎兵连的侦查前锋,而四排则作为预备队,连部的指挥和后备则设在一排。为加强火力,特地给二排增加了两支小回旋炮和几把线膛铳加强火力,因为兰石号倾覆,上面的驮马大多沉到海底了,现有的马匹都是战马,便给了一头从附近村子拉来的兕来猎兵一连驮运物资,正好奈师德要接回旋炮组下排,便先让兕驮着回旋炮、铳和弹药先拉到二排里。而椰雫溪则是突发的意外状况。
回营的路上,也奢仍然一刻不停的骂着椰雫溪。博安看着这一切,悄悄的对奈师德说:“这孩子性格真好,要是我妹妹干出这档事我早拿皮带抽她了。”奈师德点头表示同意。
回到营地,众人却差不多吃完了。奈师德和随行的炮手们已吃过饭,博安便让人给也奢和椰雫溪再弄了些米饭吃。
椰雫溪一到营地,又被吴林骂了顿,众人这时才得知吴林是椰雫溪的父亲。吴林几欲动手打她,都给也奢劝住了,这才作罢。
奈师德领着炮手安排了住宿,便乘着众人都围在火前,细细的说了明日的作战计划,让挑了几个枪法准的将线膛铳和弹药拿了,又交代了各个班的任务。
椰雫溪挨了几顿大骂,焉了一小会儿,便活跃起来了。先是跑到珊粲婕身边,看她用魔力准备着明日的各类急救器材,一边聊天,一口一个“姐姐”嘴甜的叫着。又跑来跑去看着排里的士兵们整理枪弹、讲解任务,不一会儿便和二排的官兵们混熟了。
现时,椰雫溪又对夷则的耳朵和尾巴大感兴趣,蹲在正在打磨铅弹的夷则旁边,问着各种问题。两人年纪相仿,孩子的天性使得他们很快便熟稔了。
“夷则夷则,你这耳朵和尾巴是生下来就有的,还是后来缝上去的?”
“生来就有的,这东西缝不了。”夷则正在将在篝火中用模具烧制的圆铅弹用镊子取出,一个个到放一杯水中冷却。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bheatan(梵梨语中的兽人)呢,可以摸摸你的耳朵吗?”
“be......什么是啥东西?”
“就是你们这样长着狗耳朵和尾巴的人啊。”
“我这是狐狸耳朵......”
“狐狸?那又是什么动物?”
两人唧唧喳喳的说着,一旁的博安看到此景也不由得笑了笑,继续在远离篝火但有光的地方整理着自己的装备。这时椰雫溪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博安抬头,却是看到也奢站在自己面前,低着头,却是好像有什么心事。
博安随着也奢走到一旁僻静的地方,也奢却是哭了。博安急忙问道:“你莫哭嘛,有什么事说了先。”也奢却是抽抽噎噎的说了起来。
原来也奢的生父并非吴林,而是菩拂云庄的现任主人,隼利德吉。隼利德吉在正式继承庄子之前,和自己的女仆、梵梨人椰霁姝发生了关系,椰霁姝怀孕生下了也奢。但德吉由于地位关系,并不想和椰霁姝结婚,便只是给了一小笔钱,让她将孩子送回村子养大。后来德吉上位,椰霁姝嫁给了刚脱离贷臣身份的吴林,生了椰雫溪。为了谋生,两人仍在庄子中做活,而椰雫溪也还呆在庄中做女仆。
“你.......你生父没照顾照顾你家吗?你好歹也是他的儿子。”博安皱眉道。也奢像是被戳中了什么似的:“那不是我父亲!”顿了顿,补充道:“博军爷,我们这样身份的喊做家生子,仍是奴仆,除非特殊,才能被当半个正生的看待。”随即自嘲的笑到:“不过是个奴仆罢了.......但是军爷,我妈妈还在庄里做工,她不知道明天大军要来了,能不能,明天能不能不要杀她,我妈妈头发很长,眉毛......”
博安为难的打断了也奢,“我们是猎兵连的,明天负责侦查和前哨战斗,正式攻打和占领是由炮兵和战列连那边负责。”“那能不能带我去那边......”“不行!入夜后不准随意走动的,况且我的军衔也不够。不过你放心,我们不杀妇孺,和其它军队不一样的。”解释了半天,方让苦苦哀求的也奢平静下来。
博安在也奢走后,和奈师德说了此事。“这也太离谱了,我妈不是正妻,除了以后不给继承,老子从小到大吃穿倒没缺过。这德吉怎么这个样子,真是冷骨头。”奈师德说完,叹了口气:“不过这状况咱们也没什么办法,希望到时候炮弹别发中,战列连的哥们攻上去时看着点吧。”正说着,有士兵前来喊到:“奈排长,吴林向导找你。”奈师德向德安无奈的笑到,“你看,又得费口舌说一遍。”
晚上九时,打更的锣声响起。营地的士兵们除了放哨的成员,都熄了营火准备睡觉。
虽然白天十分炎热,但广南的夏夜,土地和树丛中却仍然颇有凉爽的气息。也奢和椰雫溪躺在稻草上,盖着一条薄麻袋。他们睡的帐篷是半敞开的,兕吃夜草打响鼻的声音不时传来,还能听到一旁夷则如同狐狸叫一般的特殊鼾声和其它帐篷中隐隐约约传来的打蚊子声。
椰雫溪在半梦半醒中抱住了也奢的胳膊,断断续续的嗫嚅了起来,“妈妈......呜呜......你不要死......”,也奢本就心事重重,未曾睡着,这时胳臂上感到椰雫溪的眼泪,心下更为不安。却仍是转过身来抱住椰雫溪,轻拍着妹妹的背安抚着。不一会儿椰雫溪便又睡着了。
也奢透过半敞的帐篷顶,斜望着天空。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夜空中繁星点点,望舒已经离开了这篇空域,只余星光。也奢看着夜空,默默的向星神祈祷着,“伟哉敕佗亚剌(梵梨传说中的众星之神)在上,愚下唯没顶稽首诚祷上云,愿我母椰霁姝所见,矢石围舞而不伤......”念着为数不多的几句咒语,也奢的心中似乎得到了些许快慰,不知不觉的便睡着了。
此时的周天,仍然同亿万年来一般,照耀着云澜。
(未完待续)
关键词: